罗宗强:追求历史的真实,倾注文学的情感
-
2020年05月05日
1932 年,罗宗强先生生于广东揭阳。尽管家境普通,在母亲的照料之下,他的整个童年仍然沉浸于欢快当中。1956 年他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,1961年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研究生,治中国文学批评史。上世纪 70 年代,罗先生一边照料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,一边从事学术研究,度过了一段颇为艰辛的时期。
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,他开始提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,主张把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、文学理论结合,研究文学思想的流变。之后他又提倡研究士人心态,主张从政治环境、社会思潮、生活方式等多方面把握士人心态的变化,进而考察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内在原因。
罗先生治学严谨而性情真挚,推崇在大量占有文献史料的基础上,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,同时融入个人的感受,而一切要从对文学作品的感性接受开始。罗先生已出版的多种著述,正是将追求历史的真实与倾注文学的情感熔于一炉的典范之作,常令读者手舞足蹈不能自已。
■ 罗宗强先生□ 曾繁田
壹 I 有生之年看不到完成了
□:罗先生建立起来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,并系统性地提出相应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,为学界所推重。您最初怎样想到要开展文学思想史的研究?
■罗宗强:开展文学思想史研究比较早。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,国内在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时,开始研究范畴、术语,对“气”“风骨”“神韵”等等这些概念加以解释,研究古代文学批评里面的一些评语。比如说李白诗“豪放”,杜甫诗“沉郁顿挫”,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,国内有不少学者在解释。我开始也想这样做,找了几十个范畴,可是做不下去,就觉得这些范畴、术语是在大量创作倾向出现以后才产生的。一种创作倾向出现了,大家感觉这是什么风格,就给它一个评语、一个概念,那就是古代文学批评的范畴。比如李白作品大量出来,大家看到了,就会讨论李白诗的风格是什么,于是就有了所谓“清新”“豪放”。
我们当代人研究那些范畴,离开当时的文学思潮、文学创作倾向来谈,就说不清楚。于是我想到,解释古代文学批评的术语,必须了解当时文学思想发展的状况,所以我就放弃研究范畴,开始研究文学思想。在我看来,文学思想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和理解,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诉求,他们认为文学是什么,文学拿来干什么,什么是好文学。
我主要研究思潮,不是研究某个人的文学思想,而是研究整个时代,或者某个段落、某个流派,那种整体的创作倾向。比如说,唐代诗歌发展到盛唐以后,进一步发展好像已经不容易了,人们开始另寻出路,各种流派就出来了。韩孟、刘柳、元白,各种各样新的倾向出现了。到了晚唐,很多创作技巧已经高度成熟,再发展已经不容易了,就出现了李商隐、温庭筠,他们表达内心细腻的感受,追求深层次的情感表现。
□:其后罗先生又倾注很多心力研究士人心态,发表多篇论文,更出版了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等重要著作。
■罗宗强:在研究文学思想的过程中,我发现一个问题:文学思想的变化和政治局面、士人生存状况有很大关系,或者说跟士人的心态有关系。古代的士人,或者现在的知识分子,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,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下,他可能会有什么思想,这很关键。所以,为了把文学思想说得清楚一点,我又去了解古代士人心态,最早是研究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,后来也研究明代。如果不把士人心态说清楚,文学思想就说不清楚,文学思想变化的根源也说不清楚。
文学思想的变化与多个方面有关,政治环境、社会风貌、生存状态、士人心态等等。比如说,明代为什么出现了许多世俗小说,像是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这些。那是因为士人受到了商业发展的影响,士人进入了世俗社会,市民的生活、市民的趣味影响了士人,导致创作倾向变了。到明代,什么都商业化了,就连民俗也商业化了。商业社会的观念意识影响了士人,作品的趣味也就变化了。
实际上我研究士人心态,倾注了个人的情感和体验,可能有些人因为这个而喜欢看我写的书,我把他们视为知音,因为我自己也特别重视那些投入其中的感受。心态研究面对的是人,那就难免是非褒贬,难免带着感情色彩。但是投入主观的情感,又必须以客观的材料作为依据,从客观、主观两方面同时用力,去体会、去贴近古人的心态。主观情感各人不一样,但客观材料是实有的,必须可靠。
我写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这本书,牵扯到对魏晋时期很多人、很多事的评价。在当时环境下,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,他们的行为,他们的内心世界,究竟是怎么样的,我尽量根据史料推测,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真实情况到底如何。以此为基础,再以自己的主观感受去领会那些士人的心态。有人评价这本书,说了两个字“悲慨”。在所有的评价里面这是我最重视的,我觉得这是真正理解我的。
□:对于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,罗先生有什么期望?
■罗宗强: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,就是主编《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》。有几位年轻老师跟我一起做,我自己选了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,去年又出版了明代。周秦两汉过去由我的一个学生做,一直没有写出来。辽金元也有个学生做,现在快完成了。目前主要是差一个清代,原本有另外一个同志在做,后来他搞行政了,就没做成。我们知道清代东西太多,诗文、小说、戏曲全都有,目前要在国内找出一位这几个方面都通的,不好找。所以将来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了,就到明代为止。
我们说,从事文学思想史研究要具备一些条件。第一,要有一定的国学基础,文史哲要打通,不单了解文学,还要能回归、进入古代那种知识体系,文史哲不分家。第二,要有敏锐的审美感受,创作倾向变化了没有,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,要能看得出来。看过大量作品以后,自己感受到的是什么,没有比较好的审美能力就判断不出来。第三,要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,否则就很难把问题说清楚,只能客观地说现象,说不清楚原因。
一种文学思潮发展到另外一种文学思潮,不是截然分开的,而是有衔接、有过渡、有相互影响。后一种文学思想一定与前面的文学思想有所牵连,有意无意,有形无形,接受前面文学思想的某些优点。它可能在倾向上和前面的文学思想不一样,但是不能说不一样就毫无关系,即便相反也存在着衔接过渡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写文学思想史,好多是写过渡期。再一个,要注意不同地域文学观念的变化并不是统一的,而是错综复杂的。研究古代文学思想,要把整体的思潮和不同地域的思潮梳理清楚。
我有个学生左东岭,他在首师大带了四五个人,搞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的变化。朝代更替之际文学思想如何变化,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。文学思想史研究我写到明代,没办法再写下去了,没有精力了。明代写了十二年,写得非常辛苦,年近九旬,让我再写清代实在不可能了。文学思想史当作一个学科,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,现在不知道,不知道。感到比较遗憾的就是,我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这套书完成了。
20 世纪 70 年代,罗宗强先生在赣南

贰 I 求真原本是学术的正常现象
□:就古代文论研究来说,罗先生对于“古为今用”的说法始终有所怀疑。
■罗宗强:要求古代文论研究“为今所用”,并非始于今天。1957 年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,至今没能很好地解决,“古为今用”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对待古代文论的思维定势。其实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,研究古代文学、古代文论,抱着平常心去求真,原本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,在其他国家这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,在我们这里却成了经久不衰的问题,反反复复讨论了几十年。
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多元的,可以有助于当前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,也可以在无形中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,还可以有助于文学史、思潮史、艺术史、社会史等研究,可以有益于今天,也可以有益于将来。从文化承传的角度说,弄清楚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,就是一种文化承传、文化积累,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。深入认识传统,这本身就帮助我们提高文化素养,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许多事物,帮助我们选择吸收传统当中优秀的部分。求真的研究,看似对当前没有直接用处,其实却是今天的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。
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所谓“失语症”,恐怕也不在于有没有自己的话语,而是在于学术层次。钱锺书先生就不存在“失语症”,这是很好的例子。这一点用不着忌讳,我们的文艺理论界经过多次波折,先是独尊苏联一家,后来又似懂非懂地塞进许多西方理论。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,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与国际文学理论界对话,谈何容易。
□:古代文论当中的一些范畴,“意境”“神韵”“风骨”等等,好像确实无法用来评判现代文学。
■罗宗强:古代文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特有的范畴、术语,因此有人提出范畴的“话语转换”问题。陈洪先生写文章说,转换非常困难:各个文论家使用某一概念时内涵并不统一;同一概念古今含义不同;概念的象喻性使得其自身无法界定。我同意他的看法。
古代文论的范畴和命题能否通过“话语转换”为今所用,我也有过一些思考。首先,古代文论每一个范畴和命题,都有文学创作思潮的背景。现在研究古代文学,常常运用古代文论的一些术语和范畴,是因为那些术语和范畴适于说明古代文学的某些特点。如果把古代文论的术语和范畴转换为现在的话语,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,用来说明今天远为复杂的文学现象,恐怕非常难。
文学是一种历史现象,文学理论也是一种历史现象,时移世易,要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,恐怕是不合理的。有人明确指出过,古代文学的语境丧失了,所以古代文论无法评论现代文学。其实,古代的不同时期之间,也存在这样的问题。拿某一个文学思潮的理论范畴,去评论另一个文学思潮的文学作品,常常并不贴切。比如用“风骨”去评定公安派,用“神韵”去批评龚自珍,不仅说不清楚,也不合理。一个范畴往往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美学要求,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,并不具有普遍意义。
就连一些属于艺术方法的范畴,也不具有普遍性。比如说吧,赋、比、兴是最早的诗歌理论范畴,但是王维、孟浩然的一些诗,兴象玲珑,无迹可寻,很难分出哪是赋、哪是比、哪是兴。如果用赋、比、兴去解读,就大煞风景。李商隐的一些诗,也很难从中看到赋、比、兴的影子。有些守旧的陋儒看不到这种变化,还用赋、比、兴去解读,结果就闹出许多笑话。
往往一个文学思潮过去之后,相应的术语和范畴就渐渐归于冷落。其中有一些可能后来还被用到,但含义已经发生变化。即使如此,它通常也只适用于文学发展的一定阶段。
□:关于如何认识古代文学,罗先生提倡“历史还原”。
■罗宗强:“历史还原”就是要弄清楚种种因素在当时的实际情况,所以必须重视史料的整理。认真、严谨、广泛地清理史料,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对历史的活生生的认识。往往通读一个时期所有现存的材料,才能感受到当时文坛风貌的大致轮廓。
复原历史面貌就是求真,它本身就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,因此“历史还原”是必不可缺的。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文学史的研究缺少一种“历史感”,有时候是研究方法不合适,有时候则是研究者自己急功近利。基础研究不应该那样急功近利,应该将眼光放得更长远,如果拉开一些距离看,基础研究显然是非常重要的。基础研究的作用是无用之用,是无用之大用。
当然,要做到完全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。当时发生的事象,留下来的材料不及万分之一,以此不到万分之一的材料去推知历史真相,绝不可能。不光是史料是否完备的问题,还有研究者的种种主观因素会影响历史面貌重现的问题。我说的“历史还原”是尽可能地依据史料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,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。
我应该算是一个感情型的人,我这种性格做不了考据。但是研究文学史追求“历史还原”,必须从第一手材料出发。如果还没有看完大量原著,还没有梳理大量资料,我是不敢动笔的。对那些重要的文学事件、文学观念,我尽力把来龙去脉理清楚。
□:罗先生还讲过,文学感受力对于了解文学史至关重要。
■罗宗强:文学本身离不开感情,作者因为感情而兴发,读者因为作品而感动。编写文学史的人如果不动感情,那么他对于文学现象如何评价呢?他对于作家作品如何取舍呢?如果真做到不受感动而能有所选择,编写出来文学史,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呢?
程千帆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文学活动,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,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,而不是理性的,是‘感’字当头,而不是‘知’字当头。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,当你首先接触它的时候,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,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。由感动而理解,由理解而判断,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,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。”程先生真是说到了问题的要害。不论是文学研究的开展,还是文学史的编写,感性接受是第一位的。感性接受就会有好恶,有好恶就有取舍,有取舍就有倾向,有倾向就存在真实性问题,谁更真实地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实际面貌,那就是问题所在。
文学史的真实只能是相对的真实。建立这个基本认识之后,我们尽量复原文学的史的面貌。1989 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,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一步工作,就是历史还原。1991 年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谈到这个问题,提出历史还原的最基本工作,是原著的解读。原著解读不光是辞语的训释,还涉及义理的理解、文化背景的了解、历史段落感等等。对于古代文论原著的理解,也必须了解当时的文学创作实际。
我想,文学史编写的“历史还原”问题,也与此类似,只是更加应该强调史料的清理,做到存世资料网罗殆尽,然后辨伪、解读。这里的史料首先是指作家生平和存世作品,如果用知人论世的方法,那么作家生平、交往等材料的清理就更加重要。作品解读不确切,就很难描画出某一作家创作的真实面貌。即使我们不用知人论世的方法,正确解读作品也必是首要的工作。
正确解读作品往往被理解成辞语、事典的训释,其实这是不全面的。真实贴切地解读作品,还包括对于作品的总体把握,包括审美感受、艺术追求、艺术技巧等等。一首很好的诗、一篇很好的散文,常常被解得味同嚼蜡。研究者缺乏艺术的感受力,当然就不可能把作品的真实面貌介绍给读者。以这样的感受力写文学史,写出来的不是文学的历史,可能是社会史或者别的什么史。
罗宗强先生在书房

叁 I 文学史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
□:罗先生曾经说:“我不知道文学是什么。”
■罗宗强:是这样,有一年在广西师大,他们让我去讲一讲,我就跟同志们讲:“我搞了几十年古代文学教学,至今为止我不知道文学是什么。”在场的一位教授说,罗先生你说过头了,文学是什么,文学概论里面不是说得很清楚吗?我说,放在中国古代它就说不清楚了,因为在古代不是以文体分的,诗文是很好的文学,奏章也是很好的文学,书信也是,甚至经学注释也可能是很好的文学。
标准不一样了。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什么标准,直到现在还没弄清楚。要是用文体来分别是不是文学,就会把中国古代大量的好作品排除在外。要是按照古代的方式把各种文体都看成是文学,那现在又不好办了,当今的报纸社论是不是文学?
中国的文体产生和演变有一个过程,这个问题比较复杂,随着时代的发展,逐步明朗起来,但是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人把它说清楚。到近代受了西方影响,在外国文学影响之下,模模糊糊有了文学的概念,但是最终也没有发展到完全模仿西方的文学概念。中国也有文学的概念,但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。
□:罗先生还说过这样一句话,“文学史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”。
■罗宗强:文学本身,作者和研究者本身,原本就是丰富多彩的,并不是刻板的、单一的。个人感受不一样,你说这个作家很好,我说那个作品不行,最根本的是自己喜欢不喜欢。个人对文学作品感受不一样、认识不一样,选择必然不一样,写史过程中做出的评价也就不一样。
现在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,千篇一律,统一教材,每个学校都开一门文学史,机械化生产,像工厂一样。新中国成立前那些大学、那些中文系并不是这样的,没有统一教材,哪个教授喜欢杜甫,他可以一学期就讲杜甫,他研究什么他就讲什么。那时候并不统一教材,没有谁讲完全部的文学史,没有啊,你喜欢哪一段,你就讲哪一段。那些学校,那些教师,特点不一样,专长不一样,不同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就不一样。
各个学校的中文系全部统一教材,所有中文系都从先秦讲到近代,全一个样,所以教师就按教材讲。假如文学史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,谁爱怎么讲就怎么讲,那中文系的课讲出来就不一样了。各个学校都有各自的特色,也可能这个学校就讲到唐代为止,也可能那个学校只讲明清。关键是教会学生学习、研究的方法,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文学史。
□:如果能这样真是太好了。老师把自己最要紧的学问传授给学生。
■罗宗强:还有个问题,现在文学史侧重于讲史,文学本身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,从中小学到大学都有这个问题。文学干什么的?文学要陶养情操、树立人格,培养善良的品质、丰富的感情和高尚的人格。文学史除了说明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事实,还应该陶冶情操。很多文学作品里面那些感人的东西,根本没有讲出来,把作品全都讲死了。一首诗拆得零零碎碎,整体感受、整体倾向、感染力,全都没有了。
以前有些老先生讲课,一首诗吟诵下来,那真是沉醉其中,吟诵完了也就讲完了。这也是一种情况,因为读诗是个感受,不那么容易讲明白。但是现代研究不太一样了,要说出所以然来。我给你举个例子,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先生有一本书叫《唐人七绝诗浅释》,那书真好!一首诗,她跟你解释出来为什么好。她会拿出类似的诗进行对比,告诉你这首诗究竟好在哪里。你跟着她读诗,就会了解,哦,感情、格调、深度在这里!
除了沈先生这种方法,叶嘉莹先生从诗的结构、细腻的层次上来讲,也是一种方法。还可以把诗拆开来,说清楚具体好在什么地方,这方面蒋寅先生的《大历诗风》这本书写得好,他告诉你大历诗风到底是什么,他说了好几个道理,结构啊,用词啊,等等这些,一一给你指出来。
□:罗先生著有《读文心雕龙手记》,这本书的主体内容是罗先生选择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里的一些范畴、词语,逐一加以解说。对于怎样讲解古代文学理论,罗先生有何看法?
■罗宗强:《文心雕龙》每一篇到底说了什么,各人认识不一样。原因之一,我想就是对于里面的一些词语,大家理解不一样,到现在为止,也没有人能说清楚“气”是什么,“风骨”是什么。我写这本书主要是想解读一些词语,在我的理解中,这些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,大家并不一定同意。比如《原道》第一篇第一句“文之为德也大矣”,到底说什么呢,大家看法就不一样,我说出我自己的理解而已。
后来因为大家都说,像刘勰这样的大理论家为什么今天没有出现?所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《从文心雕龙看刘勰的知识积累》,关注刘勰的素养。从刘勰身上,我们既看到广博的知识,看到缜密的思维,还看到敏锐的感受。这些素养对于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不可偏废,单就知识积累来说,刘勰看了多少书啊,受了多少影响啊,我们现在看过哪些书,我们望尘莫及。
我想,读古代文论,同样首先应读懂原著。一种文论在什么样的文学创作背景下提出来,历代对这种论说都有些什么评价,弄清楚这些之后,才谈得上衡量其文论史上的价值。或许我们会有所收获,并且从收获当中受到启发,产生联想,在考虑新的文学理论问题时,就会对我们有所帮助。但那只属于知识积累的一点,真要有所建树,道路长得很,不仅要广泛阅读、大量积累,还要对文学的发展有深入的了解,最好再懂点创作,避免从理论到理论,空泛不着边际。当然,我不是理论家,门外谈论这个问题,行家们一笑置之便是。
2006 年,我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为研究生开《文心雕龙》导读课。当时开课的目的是想让学生读懂这本书。我介绍了几种注释本,让他们对比着读,查阅有关材料,自己做出判断,认真解释其中的范畴、词语。最后,也说出我的看法。开课之后,写了《读文心雕龙手记》那本书。我在南开大学为研究生开《庄子》导读课,精读内七篇,也是用这种方法。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《庄子》注释本,让他们对比着读,联系外杂篇的一些问题做出判断,同时查阅相关材料,了解与不同注释有关的一些思想史现象。

肆 I 嵇康从未进入庄子“坐忘”的境界
□:罗先生的书架上摆着那么多《庄子》注释本的影印本,可见先生多么钟爱庄子。能否请罗先生谈一谈庄子的精神境界?
■罗宗强:庄子是主张返归自然、泯灭自我的大宗师,他把物我一体、与道为一看成人生最高境界。庄子心目中的至人,世事无所系念于心,因而与宇宙并存。要做到这一点,就要游于形骸之内,而不是游于形骸之外。游于形骸之内,是游心,就要“以死生为一条,以可不可为一贯”,既泯灭是非界线,无可无不可,又泯灭物我界线,身如枯木、心如死灰,达到坐忘的境界。进入这个境界之后,便可以随物化迁。我不必执着为我,任自然而委化,一切不入于心。
庄子的妻子死了,他鼓盆而歌。庄子处穷闾阨巷,槁项黄馘,而泰然自若,完全进入了一种内心的境界,舍弃人间一切的礼仪规范、欲望要求,“树之于无何有之乡,广莫之野,彷徨乎无为其侧,逍遥乎寝卧其下”。心与道合,我与自然泯一,这就是庄子的追求。
庄子这种追求与其说是人生境界,不如说是一种纯哲理的境界,在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。庄子多处提到生之如梦,梦亦如梦,都说明这种纯哲理的境界难以成为实在的人生。他是要以这样的精神境界去摆脱人间的一切痛苦,是悲愤情绪走向极端之后的产物。
后人从不同的角度领悟庄子的返归自然,返归自然而寡欲,返归自然而纵欲,返归自然而无欲,等等。但是真正做到物我两忘,身如枯木、心如死灰,即便槁项黄馘,仍然泛若不系之舟,游于无何有之乡,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,并不是一个人间境界。嵇康是第一个把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的人。
□:嵇康怎样把庄子的哲理境界变成了人间境界?
■罗宗强:嵇康把庄子的理想境界人间化了,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实有的境界,从道的境界变为诗的境界。庄子槁项黄馘,而嵇康却是“土木形骸,不加饰厉,而龙章凤姿,天质自然”“岩岩若孤松之独立,其醉也,傀俄若玉山之将崩”。他和庄子一样不加修饰,完全是自然面目,但又没有半点枯槁困顿的形态。
最重要的是,嵇康把坐忘的精神境界,变成了优游容与的生活方式,“放棹投竿,优游卒岁”“操缦清商,游心大象”“思友长林,抱朴山嵋”“流磻平皋,垂纶长川”“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”等等这些。
嵇康所追求的优游闲适,体现着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,是一种随情之所至的淡泊生活。建安士人感叹时光流逝、人生短促,往往及时行乐、享受人生,而嵇康则是在对于自然的体认中走向人生。嵇康“操缦清商”是在体认自然中展开的,“放棹投竿”也是为了游心于寂寞,“垂纶长川”则使人想到庄子的避世。
嵇康从优游容与的生活当中所要体认的,正是庄子所要追求的道的境界,所谓“游心大象”“含道独往”。但是,嵇康的游心太玄、求之于形骸之内、求意足,已经不是梦幻,不是不可捉摸的道,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,是一种淡泊朴野、闲适自得的生活。在这种可感可行的生活里,他进入游心太玄的境界。
“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”是一种体验,在无拘无束、悠闲自得中忽有所悟,心与道合,我与自然融为一体。这种心境难以言状,不能言传的意蕴就在“目送归鸿”当中,前人称其“妙在象外”。有悟于道,俯仰自得,从中感到一种宁静,又回到现实中来。嵇康从未进入一种坐忘的境界,他所追求的只是平宁的心境、淡泊的生活。
嵇康追求自由自在、闲适愉悦、亲近自然、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。这种人生摆脱了世俗的系累和礼法的约束,但又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,有朴素真诚的亲情慰藉。在这种生活里,嵇康得到精神的自由,达成他自己的真实存在。嵇康把任自然的生活作为理想人生去追求,引向如诗如画的现实人生。庄子纯哲理的人生境界,由此变成了具体的真实人生。
罗宗强先生在南开寓所接受访谈
□:嵇康把庄子的哲理境界变成人间境界,可是嵇康“从未进入坐忘的境界”。庄子所讲的“坐忘”究竟是怎样一种境界?
■罗宗强:《庄子·大宗师》说“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知,同于大通,此谓坐忘”。关于“坐忘”有许多解说。崔撰说:“端坐而忘。”这个挺含混的,忘什么,忘身还是忘心?忘内还是忘外?司马彪说:“坐而自忘其身。”他理解是忘“身”,忘形体之“我”,是否兼忘心呢,没说。郭象说得明确一些:“夫坐忘者,奚所不忘哉!既忘其迹,又忘其所以迹者,内不觉其一身,外不识有天地,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。”就是既忘身,又忘知。
成玄英说:“枯木死灰,冥同大道,为此之益,谓之坐忘也。”身为枯木是遗弃生机,心为死灰是遗弃思虑,也是身心两忘的意思。朱得之借用《庄子》里的话,把这点说得更清楚:“坐忘者,不特忘形骸,并其知亦忘之矣,犹曰‘吾丧我’。”这个“吾丧我”,是《齐物论》篇讨论无差别的话,就是忘身忘知,与大道一体,无所差别。
与“坐忘”意涵相似的还有“心斋”。《人间世》篇这样写:“若一志,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,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。听止于耳,心止于符。气也者,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,心斋也。”吕惠卿说:“心斋者,无思无为而复乎无心也。”郭良翰引李宗谦说:“如己心里有一段欲斗争他,欲感动他,欲委曲他的意思,便不虚,便被他牵去,便是坐驰。……以道集虚,心中空空净净,了无门户,了无垢毒,外不狥耳目,内不起心知。”其实“心斋”也就是“坐忘”,心中空无所有,物我两忘,与道为一。
相似的意思,《在宥》篇也出现了:“心养!汝徒处无为,而物自化。堕尔形体,吐尔聪明,伦与物忘,大同乎涬溟。解心释神,漠然无魂。万物云云,各复其根而不知。浑浑沌沌,终身不离。”吕惠卿说:“涬溟,则气之虚而待物也,吾与物皆忘而大同乎!”郭良翰说:“解心,解去其有心之心;释神,释去其有知之神也。”马鲁说:“心养,犹心斋也。能养心于至虚,但安处无为而物自化矣。”这说的也仍然是“坐忘”。《在宥》“心养”这段话,实际上是《大宗师》“坐忘”那段话的重复,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。
“坐忘”与“心斋”是庄子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:物我两忘,与道为一。这种追求,可以说贯穿庄子的全部思想。这种境界也就是《应帝王》篇所描述的壶子的最高境界:“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委蛇,不知其谁何,因以为弟靡,因以为波流,故逃也。”所谓“未始出吾宗”,就是未离于道,壶子所显示的是与道为一的境界,自我完全消失了,处于一种空无所有的状态,与万物为一体,随万物之变化而变化,以为什么就是什么。
庄子反复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这一境界,如《大宗师》篇说:“吾犹守而告之,三日而后能外天下;已外天下矣,吾又守之,七日而后能外物;已外物矣,吾又守之,九日而后能外生;已外生矣,而后能朝彻;朝彻,而后能见独;见独,而后能无古今;无古今,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”
《逍遥游》篇则从“无待”的角度加以表述:“乘天地之正,而御六气之辩,以游无穷者,彼且恶乎待哉!”自我既与道泯一,自我的存在也就不重要了。庄子并不重视生命存在的意义,一视生与死,以死生为一条,他借子祀等四人之口说:“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,吾与之友矣。”
庄子以为,闻知死而惊叹,乃是不正常的事。“夫大块载我以形,劳我以生,佚我以老,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,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冶铸金,金踊跃曰:‘我且必为镆铘!’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而曰:‘人耳!人耳!’夫造化必以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为大炉,以造化为大冶,恶乎往而不可哉!”
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,庄子并不追求长生。他写《养生主》篇,那养生的主旨,不是延年益寿,而是顺死生之自然,舍弃人为干预,生安于生,死安于死,“适来,夫子时也;适去,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,哀乐不能入也,古者谓是帝之悬解”。自然而生,自然而死,一切任其自然。
《养生主》篇说:“缘督以为经,可以保身,可以全生,可以养亲,可以尽年。”庄子的这一段论述,常被后代作为庄子重服气养生的证据,其实庄子的本意并非如此。保身、全生、养亲、尽年,都是终其天年的意思,顺自然以终天年,并没有人为养炼以求长生的含义。“缘督以为经”,就是循中道以为常,所谓“中”,就是不旁倚。司马彪注:“缘,顺也;督,中也。”“督”的原义是指督脉,自尾间沿脊椎以至泥丸,因其处身之中,故借以训中。
陆长庚说:“缘督只是借喻。庄子书论性字处居多,养生只是说性。”他明确地认识到“缘督”并不是指缘督以行气,只是借以喻中。更重要的是,他把这种理解归到庄子的根本思想上来,提出庄子论养生只是说性,而不是说命。这是非常有见地的。说性,着重人生境界的修养,侧重精神方面;说命,则重在益寿延年。
“坐忘”“心斋”“缘督以为经”,都说明庄子的人生追求在于与道泯一。与道泯一,就是物我两忘。物我两忘必然轻自我、轻生命,与医家追求益寿延年,与神仙家祈求长生不死,都是不同的。庄子推崇“真人”,他描述说:“古之真人,其寝不梦,其觉无忧,其食不甘,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,众人之息以喉。”“古之真人,不知说生,不知恶死;其出不欣,其入不距;翛然而往,翛然而来而已矣。”想想看,混一天人,泯同彼我,入于不死不生,自我存在于道中。这就是“坐忘”。
□:中国古代诗人当中,有谁达到了这种境界?
■罗宗强:陶渊明常常达到物我一体、与道冥一的境界。在中国文化史上,陶渊明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。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,成为自然间的一员,不是旁观者,不是欣赏者,更不是占有者。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,无复独多虑。”他与自然是如此亲近。
在会稽名士的诗文言谈中间,我们看到山川之美是草木蒙茸,那是满怀雅趣的士人眼里的明秀之美。而陶渊明所写的山川全是田家景色,淳朴的村民活动于山川之中,人与自然融为一个整体。陶渊明并不对山川作纯粹的审美鉴赏,而是写山川在他生活中、在他心里的位置,他在其中体味着美感。
《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》只是写气候,山中秋气来得早,写一部分自然景色,只此而已。但是读起来却感同身受,那是因为他写的是心灵与自然的交通。山间景色,是他心中的景色,他没有说它美,也没有说它不美,没有说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。陶渊明并不像前辈会稽名士那样,在山川秀色面前不可已已,说一些情何以堪的话。但是他却有着更深的眷恋,那是他的山水,他的天地,和他同生命、同脉搏,和他的身心原是一体。
《归田园居》同样如此,村落、炊烟、田野、月色、山涧、榛莽,都和他的心灵相通。他就在这安静的山野间生活,一切是那样自然,仿佛原本都是如此存在,那样合理,那样真实,那样永恒。心灵与自然,全融合在这永恒的真实中。“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。虽未量岁功,即事多所欣。耕种有时息,行者无问津。日入相与归,壶浆劳近邻。长吟掩柴门,聊为垅亩民。”这样的心境,唯有领悟到了大自然的不息生机正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归宿,才有可能出现。草木飞鸟,细雨清风,各得其所,我也在自然里自得自足,成了自然的一部分。“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”之所以传诵千古,就在于那难以言说但是确实存在的令人神往的和谐。
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这里物我泯一,分不出心与物的界限,一片心绪不知落在何处。人与菊、与山、与鸟,和谐地存在,仿佛宇宙原本如此安排,日日如是,年年如是。何以如是,不可言说也无须言说。这种心物交融的境界,不易描述、不易图画。多少人为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心驰神往,可是从来没有一位画家,能够画出那个境界。那是宇宙一体的美,大美无形,很难用言语、图画表达。
物我一体,心与大自然泯一,是老庄的最高境界,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,而玄学思潮起来之后,陶渊明是第一位真正达到这一境界的人。陶渊明实在是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了,一切都生生不息、自乐自得: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。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。”
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境界,就在于他真正持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,并且确实做到了委运任化。人生活在社会里,衣食住行都有各种关系制约着,那就必定有失意,有困厄,有苦闷,有悲哀,有种种祸患。当生老病死、祸患困厄到来的时候,如果不能以委运任化的态度对待,就会陷入烦苦怨愤,那就无从返归自然,更不可能达到物我泯一的境界。
庄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,玄学家没有做到,陶渊明却做到了。生命短促的悲哀,灾祸降临的不幸,他都泰然处之,一一任其自然。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后来有两位诗人也常常能在一个短时期里做到,一位是苏轼,一位是晚年的白居易。大概也是因为在这一点上相通,他们两人都十分推崇陶渊明,并且两人晚年都写了和陶诗。
笔者与罗宗强先生合影留念

后记
如今罗宗强先生八十有五,平日他不怎么出门,也不再做研究,有时看看书,有时跟老朋友通个电话。只在天气好的时候,拿一根拐棍下楼去走走。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“晃晃荡荡没什么事”。当日在客厅里坐下来,罗先生对笔者说:“现在什么研究都做不成了,记忆力不行了。上午看书,下午就忘记。现在,唉,无所事事。那天上海的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,跟我说,他现在搞不了研究了。我和他说,我也是啊,别研究了,老了。”
访谈过程中,罗先生说起自己非常喜欢《庄子》:“要是能达到庄子那种心态真好,可是做不到。不为物喜,不为己悲,整个心啊,不系之舟,无所着落,一切全都不在乎。无所约束,无所牵挂,一任自然。做不到。”而在笔者看来,罗先生如今正是“不系之舟”,一任自然。那天中午笔者赖在罗先生家吃午饭,尝到罗先生亲手做的鸡汤和红烧肉,又吃了许多师母煮的饺子。可能罗先生知道自己并非“一切全都不在乎”,吃饭时他几次说道:“人生啊,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“坐忘,就是内心空灵,没有思虑,忘记自己。我和万物一体,万物是我,我是万物,花也是我,我也是花,泯一于道,万物都是道的体现。”此刻,当笔者录下罗宗强先生这段话,想起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所写,“固知一死生为虚诞,齐彭殇为妄作”。死生大亦或不大,古往今来人们的心态纵使有境界上的差别,心境波动变化之间,到底还是休戚与共吧?
补记
今天下午,4月29日13时50分,罗宗强先生仙逝,享年九十岁。回顾罗先生对于学术的追求,对于庄子的钟爱,对于物我的思辨,对于死生的慨叹,重读先生当日所言“我应该算是一个感情型的人”,不禁慨然。此前有缘两度登门拜访,受教于罗先生。其后不揣冒昧邮件往来,先生也曾赐赠新书。笔者深感罗先生平易亲近,五年之间未能再往拜见,抱憾!此刻却想起钱穆先生一段话,大意是:白驹过隙,忽然而已,不失其赤子之心,即能坦然。
(本文经罗宗强先生审定,承蒙罗先生亲笔批改,谨此拜谢。感谢南开大学中文系卢盛江、张峰屹、卢燕新、可延涛四位老师对先后两次访谈给予支持。笔者采写、整理,参考相关著作,在此一并致谢。)
原载《儒风大家》
特别声明:
本文为人文传媒网平台“人文号”作者上传并发布,仅代表作者观点,与“人文号”立场无关,“人文号”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
如有文章内容、版权等问题,请联系人文传媒网。
联系邮箱:www_rwcmw@163.com












.png)






 分享
分享 举报
举报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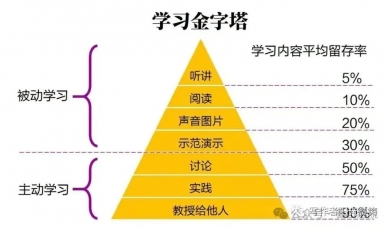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